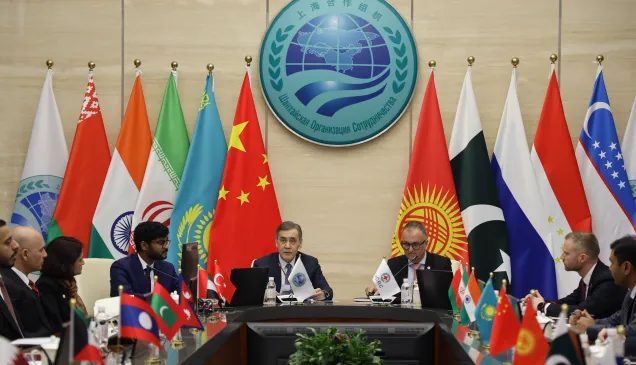军事行动国际法规则发展新趋势

——参加2016年军事行动国际法规则高级研讨班后记
鲁大海
国庆节前夕,笔者参加了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瑞士陆军共同主办的"军事行动国际法规则高级研讨班(Senior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Rules governing Military Operations,SWIRMO)"。作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国际人道法传播领域的旗舰项目,军事行动国际法规则高级研讨班自2007年起已举办多届,该项目重在邀请中级作战指挥军官(上校至准将军衔)从行动和法律结合层面探讨国际规则在武装冲突和其他暴力情势中的适用。自2002年笔者第一次参加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组织的类似武装冲突法研讨班算起十几年已经过去了,在这期间武装冲突的形态以及作战方法和手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给国际人道法的适用带来很多困难和挑战。尽管近年来作者不再直接从事国际人道法的理论研究,但对这一传统公法领域的动态变化和发展一直保持着不改的初心和浓厚的兴趣,这次偶然参加研讨班给了我一个难得的重新回顾国际人道法以及审视这种变化挑战的机会。
由于研讨班是按照"查塔姆守则(Chatham House Rule)"组织的,本文不会引用任何参加会议的个人或组织的观点看法,对一些问题的讨论也不代表本人所属组织或机构的任何立场,文章内容本身也超出了此次研讨班的范围(比如也涉及到平时军事行动国际规则的适用),更多是以此为引子分享一些个人的体会和看法。考虑到国际人道法适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国际人道法规则内容的认知(IHL Awareness),更多地分享和交流这种观点看法本身自有其价值和意义。由于时间匆忙,对这种挑战和变化的梳理只是粗浅和初步的,主要分析对国际人道法等军事行动国际规则适用产生重要影响几个突出领域,无意覆盖国际人道法规则发展的方方面面。
首先是武装冲突形态的变化对战争权(即诉诸武力的权利jus ad bellum)和战时法(jus in bello)的适用都带来挑战。对于交战双方清晰可辨的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性武装冲突或非国际性武装冲突,交战各方在冲突开始前享有的诉诸武力的权利以及冲突开始后具体国际人道法规则的适用相对比较简单。调整诉诸武力的权利的国际规则以自卫权和《联合国宪章》第七章下的集体安全体制为基础,即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利主要包括自卫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两种情况。调整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战时法规则以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和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为重点,也包括传统的"海牙法"公约体系,即1899年和1907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有关战争法的公约;调整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战时法规则以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共同第三条和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为重点。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两个附加议定书的突出特点是既包含了调整如何作战的规则——即有关作战手段和方法的规则,也包含了保护战争受难者的规则,代表了日内瓦公约体系和海牙公约体系的融合。此后的国际人道法条约延续了这一特点,比较重要的比如1980年《常规武器公约》及其五个附加议定书、1997年《渥太华公约》、1998年《国际刑事法院罗马公约》、1999年《文化财产保护公约议定书》以及2000年《儿童权利公约关于儿童卷入武装冲突问题的任择议定书》。
在条约法之外,适用于国际性武装冲突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这两类规则都有习惯国际法规则与条约法规则同时存在。习惯独立于条约之外与条约同时存在,尽管又是条约已经吸收了习惯法的内容,这一点已为国际法院"尼加拉瓜军事与准军事活动案"等多个国际司法判决所确认。而且,与只约束当事国的条约相比,习惯法规则的最大优势是其对所有国家均具有拘束力,除非一个国家从一开始即为持续反对者。尽管,在19世纪中叶以前,国际人道法的规则作为习惯一直存在。与条约法不同,由国家实践和法律确信两个要素决定的习惯法规则的存在不容易确定。在习惯国际人道法规则编纂方面值得一提的是,经1995年第26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大会授权,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于1995年起组织专家对国际人道法习惯规则进行研究,期间经过多轮征求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意见,最终于2004年出版了两卷本的《习惯国际人道法》,这是二战以来首次对国际人道法习惯规则进行的系统编纂。
这些由习惯和条约构成的国际法规则构成了国际人道法体系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一状态随着科技进步引发作战手段和方法的改变以武装冲突形态的变革被逐步打破。除了武装冲突在物理空间向网络、太空扩展以外(后面还要提及),最突出的一点是从"9·11"和由此引起的阿富汗战争开始,非国家行为体(non-state actor)的卷入使得现有法律适用的边界变得不那么清晰。
一方面,从战争权的角度,能否将传统的国家间自卫权直接适用于非国家行为体,还是只能适用于支持(harboring)这种非国家行为体的国家,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四款明确规定:"禁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第51条关于自卫权的规定通常将引起自卫权行使的"武力攻击"限于国家实施的武力攻击。当一个国家针对非国家行为体的行为发动"反恐战争"的时候,所针对的这种行为是国际犯罪行为还是武力攻击?行使自卫权的对象到底是谁,都引起了理论上的争论。此外,十几年来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措辞的变化从集体安全制度下武力使用的另一角度也反映了这一变化。在针对恐怖主义和海盗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中,越来越多地针对恐怖组织、海盗等非国家行为体使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措辞或类似说法。特别是自2008年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各国派武装力量赴亚丁湾和索马里海域执行反海盗行动以来,这种措辞的使用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从战时法的角度,如何定性这种针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武装冲突产生了规则适用的困惑和挑战。"反恐战争"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它只能或者是国际性武装冲突,或者是非国际性武装冲突,当然不排除在混合型的武装冲突中根据不同交战方主体属性可能适用完全不同的规则。这种法律适用的争议直接影响到被拘禁人员的法律地位和其所应享有的人道待遇。最明显的就是美国拒绝给予关押在关塔那摩基地的塔利班被拘禁人员战俘待遇,这在国际社会饱受诟病和引起很大争议。美国撤离伊拉克后产生的跨越叙伊两国边界的"伊斯兰国"现象更加模糊了法律适用的边界。只需想象一下现在的叙利亚武装冲突,包括了叙利亚政府军、叙利亚多个反政府武装、"伊斯兰国"武装力量以及这些力量背后的美英联军和俄罗斯武装力量等冲突各方,如何定性这样的武装冲突和在不同冲突各方之间适用恰当的战时法规则,无疑是一件让国际法律师挠头的事情。

其次,作战手段和方法的革命性变化既对现有规则的适用带来挑战,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规则的真空。尽管近年来在海战法和空战法领域先后通过了《圣雷莫国际海上武装冲突法手册》以及《空战和导弹战国际法手册》等非具法律约束力的文件,这种革命性变化最明显还是体现于网络空间的作战行动以及无人机的作战使用。虚拟网络空间打破了传统主权国家之间的边界界限,技术上难以对网络攻击追根溯源更是加剧了这一地带的模糊性。这种背景下,在平时非武装冲突情况下使用网络攻击对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害是否构成《联合国宪章》所称的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武力攻击"从而引发自卫权的适用,构成多大的损害才能构成等同于自卫法上的武力攻击的情势,在武装冲突中作为作战手段和方法进行网络攻击如何适用现有的战时法规则,这些问题或者构成对现有规则的挑战,或者本身就没有明确的答案。在存在"规则真空"的情况下,谁来主导制定普遍适用的国际规则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可适用于网络战的国际法的塔林手册》代表了一些国家的观点,但远不代表已经形成普遍适用的规则。
在武装冲突状态下作为作战方法和手段使用无人机似乎仍然可以根据冲突的情势不同适用传统的战时法规则,产生法律适用麻烦更多是因为在远离战场情况下在非冲突国家境内使用无人机以及在平时使用无人机执行作战任务,这即涉及到侵犯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也在很多情况下构成明显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未审判即处决"的行为。可以预见,当未来地面无人作战系统(机器人)和水下无人作战系统(无人潜航器)被广泛用于武装冲突的时候,又将对现有规则的适用产生新的挑战和影响。而且,从军事行动国际规则的角度看,这种影响和挑战并不局限于战时法领域。随着科技的进步,当无人机、水中无人自航器被用于平时军事行动成为常态,也将对国际海洋法、国际航空法等其他公法领域产生重要影响。
军事行动当然不局限于战时武装冲突,和平时期使用军事力量进行撤侨、护航、执法、国际灾难救援、国际维和等诸多军事行动也都涉及到不同领域国际规则的适用,特别是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更是要考虑可适用的国际法规则制定不同的交战规则。以维和行动国际规则的适用为例,随着维和行动由原来传统的授权单一、作为国际性武装冲突中完全中立一方的维持和平行动(Peacekeeping operations)发展到现在授权更为复杂、任务多样化的和平行动(Peace operations),其适用的国际法规则也越来越复杂。《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作为维和行动的法律依据和基础已经有很多讨论,1999年联合国秘书长颁布的公告为维和行动适用国际人道法提供了具体指引,联合国与东道国之间的部队地位协议以及联合国与出兵国签署的备忘录是调整各方法律关系的重要方面,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指针以及针对特定维和任务的任务规则指令和交战规则为维和部队开展军事行动提供具体操作指南。随着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全面参与执行保护平民、执行和平协议、恢复法律秩序、遣散武装人员、举行大选等各种战后重建任务,法律关系的主体和法律适用环境更加复杂。目前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随着安理会授权的增强,维和部队交战规则的制定需要考虑更为复杂的因素。除满足自身安全需要外,保护授权指定组织和人员安全使维和行动武力使用远远超出传统自卫的需要,近年来维和部队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履行授权以及维和部队自身受到攻击的情况备受关注。二是维和行动中出现的性侵等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性丑闻案例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也引发了追究维和部队人员刑事责任以及联合国作为国际组织承担国际责任的讨论。
最后,海上军事行动国际法规则不仅包括作为国际人道法组成部分的海战法,海军作为"养兵千日、用兵千日"的特殊国际性军种,以国际海洋法为基础的调整平时海上军事行动的国际法规则与海战法同等重要。特别是近年来海洋边界争端和纠纷大量存在,海盗、海上武装抢劫等海上犯罪行为频发,在使用军事力量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国际法规则的适用尤为重要。对这些规则的不同理解和解释适用是产生海上安全事件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执行"航行自由计划"行动引发冲突对抗就是一个重要体现。此外,在使用海军力量采取执法措施的时候容易引起对这一行为进行法律定性的争议,即这是依据国内法使用武力的国内法意义的执法行为,还是构成《联合国宪章》下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的行为。意大利诉印度的"Enrica Lexie"仲裁案仍在进行之中,这一案件将成为这一领域值得关注的一个重要案例。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参与和影响甚至在个别领域主导国际规则的制定是应有之意,军事行动国际法规则的创制和发展理应包括其中,但现实并不乐观。客观上,军事行动作为一个特殊领域不是能够被广大社会力量所接触的社会实践,军队本身又缺乏对此进行研究的组织体系和专业力量,这必然对我们在这一领域国际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和话语权产生影响。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入世"谈判促进了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领域国际规则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南海仲裁案"有国际海洋法领域启蒙运动的意义,笔者实在不希望看到在国际人道法领域发生类似的推动事件,不希望战争来临才发现"法到用时方恨晚"。要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还需要政府、学界等军地各领域付出更多的努力。